Opus 2 - Jeu du rapt
- Mar 31, 2016
- 3 min read

以下算是給這半年一個交代,也是給予自己想新東西的壓力。 死啦什麼心的創作想法是基於十年前左右姚大鈞所寫的「泛具象音樂論」的應用,利用音樂的泛具象特質(而非古典浪漫主義的煽情或歌詞)來描寫我的人生經歷中所想到的故事,間接地表現自己平常在想的一些關於人與世界的小事與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抽象概念。使用音樂而非文字一方面我並非作家文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只會用吉他發出我喜歡的聲音,一方面也是在宣告自己並沒有要嚴肅的討論這些話題,沒有要得到什麼答案,也沒有要聽眾一起來關心這些故事裡外的意義。然而,回台後決定要開始玩團時在思考著要玩什麼樣的東西(自己覺得)比較有趣,而這樣的創作形式則是目前想到的一個以往創作瓶頸的出口。然而,雖然以行動劇、舞蹈與劇團等的概念卻不以這些藝術形式做演出乃是基於作為一個音樂樂團的本質,不希望以任何聲音演出以外的形式稀釋了「泛具象音樂論」的實踐,同時也有著自己創作的挑戰性,並且像是在說我們並沒有宣稱這是一個新的音樂藝術形式(比起那些意欲天馬行空卻總是走不出死胡同的各種nonsense,我比較喜歡有個框架來限制自己,反正我們這群愛踩線的北七總是會溢出框框之外)。 團名死啦什麼心就像許多人知道的,來自多年前我與小帕對重組這件事的約定,然後經過拉拉惡趣味的翻譯。然而沒有負責彈低音吉他只是因為在剛回來時聽完紙巾王朝練團後覺得黃尾彈的比我好。每個器樂有自己基本的司職,然後適時地交換位置,來自幾天前剛過世的克魯伊夫的全能足球想法,沒有樂團基本款以外的樂器則是同時作為演出方便性的考量以及對於手上掌握的樂器的挑戰。音樂構成的素材來自我自己喜歡的日本噪音迷幻、極簡主義、上個世紀初的俄國新未來主義、拉美五零年代的新民歌運動、中東歐共產國際的曲調、天主教彌撒聖歌與不能避免被影響的各類型歐美台灣流行音樂,使用上配合著背景故事,利用自由爵士的方式用這些語言(其中包含著許多的人生經歷)將每個樂章編寫出來,抽象樂理的玩味以類似極簡主義作曲家的趣味玩弄符號與抽象音符的對稱性與針對人們聽覺慣性做奇偶性編排錯置,然後依照頻率分佈來安排每個器樂所負責的空間感。樂團玩到一半時開始賦予這個樂團本身的故事性,第一次演出後封聖與第二次演出被降格打入地獄即是這樣的惡趣味。類似的概念同樣套用在演出,作為樂曲的「掠婦遊戲」與作為表演的「掠婦遊戲」並不完全一致:前者算是半完成的曲子;後者則是基於前者的半完成的反省,即是原來應該得到某種程度救贖的結局不如預期,所以利用「我們宣布進入幸福狀態」的二、三樂章作為素材編寫後面那段承受不住的自嘲劇本。這個投機的想法是以寺山修司在電影與戲劇使用同樣音樂為本來為自己的偷懶做背書,然而表演失常的結果或許可以視為一種投機必然得到的報應。 聽眾的口味與聽音樂的習慣也是包含在創作的考慮之中,儘管大部分的時候還是以自己還有同溫層的朋友為主,偶爾在曲子裡跟聽眾開開玩笑(雖然不一定都有被發現,像是第一次表演之前朋友問我這樂團是玩什麼的時候我都會說極簡主義,然後在「我們宣布進入幸福狀態」的前頭安排了Steve Reich的music for 18 musicians片段結果沒有人聽出來XD)或是跟熟人聊天,就當作是路西法不為人知的溫情。 雖然可以解釋得更詳細但是打到一半就懶了,我自己對於死啦什麼心這個團的存在大概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半年來雖然沒有做到完美有著潔癖我的感覺有點北送,不過這段時間還算是過得不錯(易澄可以聽出這麼多藏在裡面的想法也算是泛具象音樂實踐的成功XD),不一一點名惹,謝謝大家這半年的幫忙與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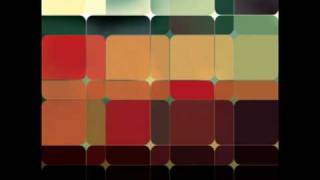








Comments